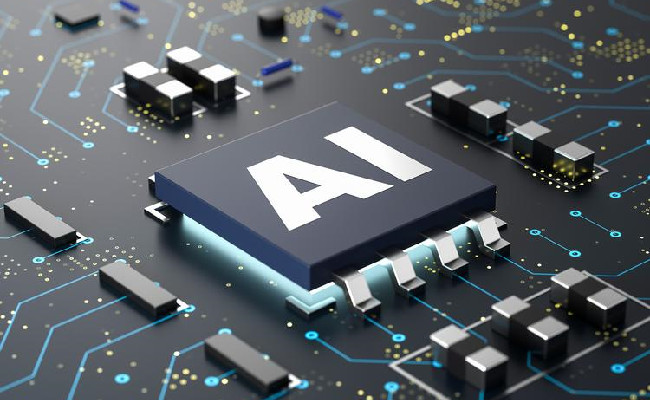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定性为作品为时尚早

资料图 王迁 近来,随着计算机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人类顶级的围棋高手,有关人工智能与著作权保护的问题获得了关注。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描述了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的过程,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似乎就有了智力创作的痕迹。那么,对这些内容在著作权法中如何定性?这一问题与著作权法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在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定性进行研究之前,应当排除那些即使源于人类,也被公认为不可能构成作品的内容。因为研究应当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特殊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是否属于创作行为,该内容是否构成作品。这一特殊问题依赖于一个前提——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符合除由人创作之外的作品构成要件。 在澳大利亚发生的Telstra公司诉电话号码出版公司案中,原告因被告复制其编制的电话号码簿而起诉被告侵权。法院认为该电话号码簿不受澳大利亚《版权法》的保护,理由之一在于它不是人类创作的结果,而是由计算机生成的。该案也被一些学者在研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时所引用。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是缺乏价值的。 如果源自人类的相同内容都不属于作品,则无论该内容是源自于动物还是人工智能,都不可能被认定为作品,只有当源自人类的相同内容属于作品时,才有必要讨论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该内容能否被认定为作品。与之相反,目前流行的一些美图软件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可将照片或图片变为印象派、野兽派等各种风格。对于进行风格转换后的图片而言,若人们并不知道它是美图软件生成的,而以为是人工绘制的,则会认定它是美术作品,即基于原作品形成的演绎作品。鉴于此,在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构成作品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在相同内容源自于人类创作的情况下,该内容在表现形式上是否构成作品。 如果相关内容是基于原有作品产生,即被主张为演绎作品,则应当判断其表达与原作品是否已存在实质性差异。例如,对于上文提及的应用人工智能的修图软件而言,由于在对照片或图片进行风格转换后,新图片与其原始状态相比已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新图片是由人绘制的,则在形式上已属于演绎作品,此时需要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以回答其是否构成作品等一系列后续问题。 对于由人工智能生成,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作品相同的内容而言,应当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判断其是否确实属于作品。 笔者认为,在对上述内容是否确实构成作品进行判断时,应当在暂不考虑主体的前提下,从相关内容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分析它们是否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此处之所以强调暂不考虑主体因素和以相关内容的产生过程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是为了避免形成逻辑循环。 从目前有关人工智能的各种报道和描述来看,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只是应用某种算法、规则和模板直接产生的结果,与为形成作品所需的智力创作相去甚远。算法、规则和模板本身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应用其产生的唯一或有限结果不可能符合独创性的要求。 以上文提及的修图软件为例,它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将照片或图片处理成印象派等各种绘画风格。仅从结果来看,多数人都会以为是画家绘制而成。然而,该项人工智能对照片或图片的处理,与绘画者根据照片或图片创作同样风格画作的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在艺术家眼中,就一张照片或图片而言,其影像或造型与印象派等风格的画作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绘制过程为绘画者留下了发挥的空间。绘画者可以凭借自己对印象派的理解和感悟,在线条的位置、粗细和弯曲度方面作出选择,在造型、明暗、阴影和色彩等因素上进行判断和处理,以表达其独特的思想感情。此现象正是独创性的体现。这就使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有别于人们严格根据算法、规则和模板实施的行为。显然,这些行为都利用了智力成果——各种方法和计算公式,如密码系统的设计和破解,五线谱和简谱等记谱方法的发明。如果将它们应用于原始材料之后,只要方法正确,无论由何人实施,获得的结果具有唯一性,就排除了实施者发挥聪明才智的可能性,导致相应的结果无法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从而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 具有学习能力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学习能力并不意味着应用这种学习成果生成内容的过程是创作,以及生成的内容是作品。它只意味着与程序设计者预先确定可直接得出结果的固有规则不同,拥有人工智能的程序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自己找出事物之中更为具体、细致的规律,它仍然属于应用特定算法获取最佳结果的过程,其作用在于从无数可能性中找到唯一或者极为有限的正确路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应用人的智能,其生成内容的过程并不涉及创作所需的智能,因此并不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日本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般认为,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不属于著作权的客体,其原因就在于人工智能自动产生的创作物(类似作品的信息),并非(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1项规定的‘表现思想或者情感的作品’,也就根本不存在对其享有的著作权。澳大利亚司法部下设的澳大利亚版权审议委员会曾在有关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报告草案中建议澳大利亚《版权法》增加计算机生成的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的作品类别,但遭到了澳大利亚版权委员会的反对,理由之一正是此类内容无法达到独创性的要求。澳大利亚版权审议委员会接受了该观点,在其发布的最终报告中,不再建议将诸如由报告撰写程序(类似于前文提及的自动新闻写作程序)生成的内容作为作品保护,而是建议创设邻接权的客体以提供保护,其用语也从计算机生成的作品改为计算机生成的内容(computer-generated material)。 在最早对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进行规定的英国《版权法》中,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被认定义为在该作品没有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该法第9条第3款规定:对(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的创作进行了必要安排的人被视为作者。然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对此指出:该规定看来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计算机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创造性贡献的情况下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否真正存在能够不借助任何人类创造性贡献而创作出作品的计算机智能,则是存疑的。同时,将该条适用于上文提及的机器人写作、作画和作曲等情形,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试问谁对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的创作进行了必要安排?是相关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还是该机器人或程序的使用者?若是前者,则其获得了对计算机程序和运行该程序生成结果的双重权利,属于重复获利,有失公平。若是后者,则意味着只要选择了某机器人或运行了某一程序就可获得著作权,显然是不合理的。 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人工智能只能按照人类预先设定的算法、规则和模板进行计算并生成内容。因此,一篇文章称机械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独创性部分所作的贡献——日益超过人类,甚至完全取代人类的精神劳动,恐怕仍然是对未来的幻想。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面临挑战甚至威胁的,将是整个人类社会,与之相比,著作权制度受到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了。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