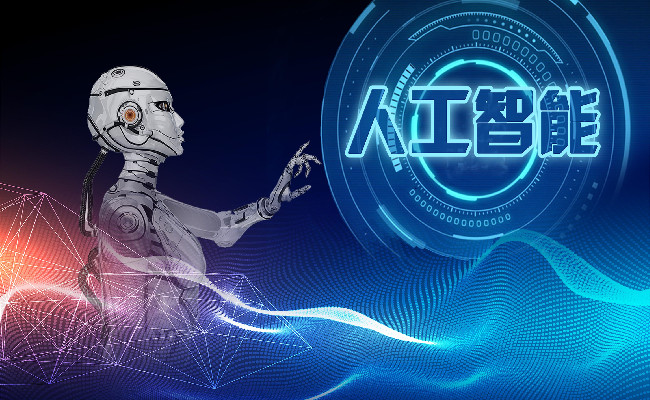影视娱乐丨浅析虚拟数字人的直播带货行为和法律问题
随着ChatGPT的大火,百度版GPT文心一言,阿里版GPT通义千问,京东版GPT言犀等相继问世,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的争议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人工智能必然不能取代人类,然而,人工智能已然取代部分人类。网络直播营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播带货,新技术驱动直播模式创新,AR技术将虚拟形象与现实直播相融合,MR技术将虚幻场景整体呈现在直播现场。实践中,虚拟数字人高度拟人化、高感知交互性、高工作效率等特点,替代标准化内容生产中的人工角色,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已成现实,已实际应用电商直播领域。本文将对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行为进行法律分析,浅析该类新型商业模式的市场发展前景、应用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如何进行权利保护。
数字人、虚拟人、虚拟数字人三者的概念有所差别,虚拟人的身份是虚构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如2023年虚拟人排名第一的洛天依。数字人则强调角色存在于数字世界,如数字孪生。虚拟数字人则是在多技术结合之下,依靠技术设备呈现,具有人的外观、动作和语音等特征,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虚拟形象,如中国移动推出的谷爱凌虚拟数字人Meet Gu、天猫推出的易烊千玺虚拟数字人千喵。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发展前景
直播带货的消费模式,带动了整个直播电商产业链联动发展,上游商品供应端(含厂商、品牌商、经销商、原产地等)销量大增,中游直播端(含直播服务商、电商平台、内容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平台以及网红达人、明星艺人、企业家及其他主播)高就业率及市场高成交额和转化率,下游需求端消费者消费满足。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年直播电商交易规模达到35000亿元,其中,抖音电商直播交易规模为15000亿元,电商直播交易规模为9000亿元,淘宝直播交易规模为7700亿元。直播电商行业企业规模达1.87万家,用户规模达4.73亿人。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直播带货的消费模式,中国市场已显示出强大的潜力和活力,加速了传统商业的数字化升级。资本加持、平台扶持与政府引导,直播电商行业正向高效、有序、理性方向发展,交易规模数据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然而,上述亮眼的直播电商交易数据是各直播平台数以万计直播间大量主播夜以继日超时长直播带货的成绩。从长远及可持续发展来看,突破人类生理极限超负荷工作模式终将被取代。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有着较高的效率和互动性,其可以通过充满个性化和娱乐性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等技术,与消费者进行个性化互动,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不仅如此,虚拟数字人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可以随时在多个平台线上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与此同时,从科技发展和技术支持上,聚焦数字建模、动态捕获和自动渲染等技术,增强虚拟人的社交性、互动性、记忆性和真实性。强化人物形象、动画语音生成、人机交互等模块的通用设计,提供多元化风格虚拟形象制作及智能交互服务,加快在电商直播、影音娱乐等场景中的成熟应用,打造场景虚拟形象代言人,已被列入多地政府产业发展重点工程。从产业发展计划安排上,数字时代元宇宙产业发展和新消费模式升级,打造元零售消费空间,推进线上商城和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支持零售企业建设AR购物、元宇宙商城等虚实融合购物空间,探索打造元宇宙智慧商圈。推进虚拟数字人在消费领域的应用落地,探索实践D2A(Direct-to-avatar,直接面向用户虚拟形象)新兴商业模式,构建人、物、场、事件耦合共生的元宇宙营销体系,已列入多地政府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目前,虚拟人直播带货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电商营销方式,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投入资金和资源,培养和推广虚拟人。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和天猫推出的星图和小苏等虚拟主播,京东推出的小爱和小恐龙等虚拟营销形象。
因此,前瞻布局未来发展新赛道,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顺应发展趋势,抢占市场先机,提前布局虚拟数字人在直播带货等商业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是否构成广告代言
1.不以真人为基础的虚假数字人能否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虚拟数字人不具有独立人格和意志,其直播带货介绍和推荐商品行为和表现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表达的内容、话术或脚本是在数据驱动基础上生成语言技术的转化。
根据《广告法》,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主体要件上,虚拟数字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构成《广告法》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
相较于自然人主播,虚拟数字人无法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不能完成商品、服务的推荐和证明工作,其在直播带货中的介绍和推荐行为,不构成广告法上的广告代言人的行为要件。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选品和试用一般由直播营销平台或直播平台运营方代为行使,但直播营销平台或直播平台运营方在直播带货行为中,并未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不符合广告代言人的身份要件,亦不能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2.以真人为基础的虚拟偶像直播带货能否被认定进行了广告代言
虚拟偶像特指以明星艺人、网络红人、知名人士等真人为基础且获得其授权许可使用其肖像和声音的虚拟数字人(以下简称虚拟偶像)。
明星艺人、网络红人、知名人士等作为公众人物,其肖像和声音等较一般人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和商业价值,相关方在使用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的肖像、声音均需取得相应的授权许可。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使用其他人肖像作为虚拟形象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应当征得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前述规定。
为此,直播平台或直播间的虚拟偶像的应用,需取得明星艺人、网络红人、知名人士等公众人物的授权许可,而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应做好事前把关,充分了解其肖像和声音的授权许可使用范围,防止授权客体被过度滥用或侵权使用。
直播间虚拟偶像的商业应用,对消费者而言,仍是以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的形象和名义进行直播带货,消费者基于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和信任在直播间消费购买商品的,可以认定构成广告代言。
《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规定,明星艺人等在商业广告中通过形象展示、语言、文字、动作等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推荐或者证明,应当依法认定为广告代言行为。广播广告虽不出现明星艺人等形象,但表明姓名并以明星艺人等名义推介商品的,应当认定进行了广告代言。
为了依法规制广告代言行为,该规定明确了明星艺人等开展广告代言行为前,应充分了解被代言企业和代言商品,查阅被代言企业登记注册信息、相关资质审批情况、企业信用记录、代言商品的商品说明书(服务流程)以及涉及消费者权利义务的合同条款和交易条件等信息,审看相关广告脚本,妥善记录对被代言企业信息了解情况、对商品体验和使用情况,保管相关广告代言合同以及代言商品消费票据等资料,建立承接广告代言档案。
因此,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在签订虚拟偶像授权许可协议时,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做好事前把关,避免承担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风险。
当然,如果企业是冒用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名义或者盗用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形象进行广告宣传的,则不属于广告代言,构成虚假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亦有明确虚假广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即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3.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不能当然认定构成虚假广告
根据《广告法》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如前所述,不以真人为基础的虚拟数字人不构成广告法上的广告代言人,不满足虚假广告的主体条件。
虚拟直播营销模式下,消费者是明知虚拟人无法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虚拟数字人在直播中介绍、展示和推荐商品,直播方式、直播商品或服务均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虚拟数字人作为主播,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操作和表达,介绍的内容是否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导致欺骗、误导消费者进行购买的行为,才是判断虚假广告的前提。如果虚拟数字人在直播中夸大或者虚构了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内容、功效、质量等信息,或者故意隐瞒其中的缺陷或风险,则会被认定构成虚假广告。
一方面,根据《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另一方面,《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加强新技术新应用新功能上线和使用管理,对利用人工智能、数字视觉、虚拟现实、语音合成等技术展示的虚拟形象从事网络直播营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并以显著方式予以标识。第十八条规定,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真实、准确、全面地发布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有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不得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存在违法违规或高风险行为,仍为其推广、引流等行为。
无论是直播营销平台还是直播间运营者,作为虚拟数字人的平台监管方还是实际使用方,均负有审核、监测、跟踪、评估虚拟数字人的直播带货行为、营销内容,规范直播运营和管理,通过技术监管和人工审核等方式及时纠正虚拟数字人的错误营销行为和内容。
如直播营销平台发现违法和不良信息,对直播间涉嫌违法违规的高风险营销行为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对涉嫌违法违规的高风险营销行为采取弹窗提示、违规警示、限制流量、暂停直播等措施,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的直播间运营者账号,视情采取警示提醒、限制功能、暂停发布、注销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
而直播间运营方应协议明确信息安全管理、商品质量审核、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义务并督促履行,做好语音和视频连线、评论、弹幕等互动内容的实时管理,不得删除、屏蔽相关不利评价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依法依规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和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消费者提出的合法合理要求。
因此,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中虚假广告行为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根据《广告法》规定,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及《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由直播营销平台(电子商务经营者)、直播间运营方(平台内经营者)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中的权利保护
1.虚拟数字人的虚拟形象和生成作品的版权保护
直播营销平台或直播间运营方创设的不以真人为基础的虚拟形象,具有独创性且作为人类智力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符合《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定义,自虚拟形象创作完成,不论是否发表,当然取得著作权,依法受《著作权法》保护。
虚拟数字人分为交互式和非交互式虚拟数字人,非交互式虚拟数字人的直播介绍和表达均来自于人类的原始设定和人类智力成果的输出,非创作性表达,不能构成作品。而交互式的虚拟数字人,在大数据、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设定基础之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表达,以演讲、歌曲、舞蹈等直播带货的节目内容表演和呈现,即使人工智能生成物(AIGC)内容存在独创性,但并非智力成果的体现,而是大数据的分析和生成,不符合《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定义,生成作品的可版权性以及是否能够受《著作权法》保护,业界尚存在争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法规和司法实践都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定和认定标准。
2.虚拟数字人的虚拟形象的商标保护
虚拟数字人的虚拟形象、名称、标志等都可以申请注册为商标,用以识别产品或服务的来源。从商业化开发和使用考虑,运营主体应在虚拟形象创设完成申请作品登记的同时,申请注册商标,以免商业开发中商标被抢注、被抄袭或被恶意侵权使用。
3.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涉及到的技术和算法的专利保护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中涉及到的技术和算法有:虚拟数字人的三维建模、动态模拟、表情识别、语音合成等虚拟数字人的建模技术,直播带货平台的直播技术、互动技术、商品展示等直播带货平台营销技术,用户画像分析、商品推荐算法、销售预测算法等数据分析和算法,以及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实现和运营等技术。未来每个直播间的虚拟数字人都会有所不同,千人千面,为保护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核心技术和创新成果,虚拟数字人的创造者或人工智能系统开发者与使用者应协议约定好专利技术的权利归属,申请专利予以保护,以免被侵权使用,而无法有效维权。
4.虚拟数字人直播间数据库和个人信息保护
虚拟数字人直播间涉及到大量的数据收集和管理,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虚拟形象的数据、直播节目的数据等。直播营销平台和直播间运营方均需加强数据安全管理,采取加密传输、数据备份、权限管理等安全措施,保障用户和数字人的数据安全;限制数据访问权限,定期清理数据,删除过期或无用的数据,避免数据泄露和滥用。
虚拟数字人直播间数据和个人信息,依法受到《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保护,直播营销平台和直播间运营方应明确数据使用规则,切实保障直播间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结语
数字空间、数字资产、数字人物以及未来即将构筑的数字世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虚拟数字人将会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和发展,应运而生的诸多法律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研究和探索。正如马云所言:数字时代,是智慧驱动,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是独立思考的竞争。为了不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人类需要不断地创造性思维和思考。
张红
合伙人
zhanghong@wincon.cn
15092232066
张红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仲裁和争议解决、娱乐法、保险法、投融资等法律事务,长期为全国大型央企、国企等企业集团提供法律服务,拥有丰富的重大、疑难、复杂的诉讼和非诉法律服务项目实务经验。
扫码添加张律师微信